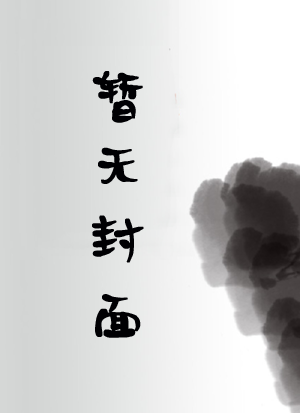前門挂着的匾,寫的是“雷起樓”,正堂上的匾,寫的是“豢龍堂”。
酣暢的金漆大字,特别有風骨,字如其人,寫字的一定是個人物。
可還沒看清楚題跋,那個柔若無骨的男人忽然擋在了我面前,眼睛往後一溜,說道:“你身後這兩個,是女人吧?把她們留在外頭,女人不能進去。”
白藿香禁不住一愣,我也一皺眉頭:“為什麼?”
那男人看着我,理直氣壯的說道:“不為什麼,這是我們家的規矩。”
其實,舊社會倒是真有這種講究——比如,一些正式宗祠,女人都是沒資格進去的,還有的地方,認定女人的天葵是最污穢的東西,會讓人倒黴,所以女人坐過的地方都嫌髒。
這都是封建社會的糟粕,我們這種傳統行業哪怕講究傳承,也沒把這種男尊女卑傳承下去。
程星河一下急眼了:“不是,大清都亡了多久了?沒女人,你們怎麼出生的?”
可那個男人絲毫不為所動,看了白藿香和赤玲一眼,眼神跟之前的水蛇腰一樣,滿是嫌惡:“你們外頭什麼規矩我們不知道,豢龍堂裡,就是不能進女人。”
赤玲半明白不明白的,一把抓住了我的手:“爹,别趕我走,爹,别趕我走……”
我也知道,入鄉随俗,到了一個地方,應該遵守一個地方的規矩,可到了這個人生地不熟的環境,讓我扔下白藿香和赤玲,我絕對做不到:“那請你伯祖出來見面也行。”
柔若無骨那個一聽這話,冷冷的說道:“那不可能——我伯祖已經二十年沒出來了。”
二十年?
程星河低聲說道:“老爺子該不會癱瘓了吧?”
我隻好說道:“如果真的沒有特殊原因,那我隻能帶她們一起進去。”
那兩個人對視了一眼,這才進去取出了兩件塑料雨衣一樣的東西:“讓那兩個女人把這個穿上。”
白藿香随手要接,可那個拿雨衣的一見,生怕白藿香的手碰上他似得,一下就把“雨衣”扔到了地上,往後退了一步,就好像白藿香多髒一樣,嫌惡的說道:“紮緊點,千萬别把你們的味道散出來。”
有必要歧視女性到這種程度嗎?
我覺得不自在,往前一步就要說話,可白藿香拉住我,低聲說道:“我是來幫你的,不是來給你添麻煩的,咱們是為了龍鱗的事情來的,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”
程星河也有些不爽,但也知道白藿香的心思,為了她真起什麼沖突,她嘴上不說,心裡肯定也不開心,于是也沒多話,把那個“雨衣”抖開,幫赤玲包裹上了。
這東西一個人還真處理不好,我就幫白藿香紮好了褲腳,那兩個人還特别仔細的檢查,就好像白藿香和赤玲是兩塊臭豆腐,他們唯恐毒氣外洩。
整理好了,他們這才說道:“可千萬别刮破了。”
說着,就進去了。
程星河撞了我肩膀一下:“你看出這什麼材質了吧?”
這好像是巨鼋的裙邊皮。
外号叫隐身衣。
倒不是真的能把人變透明,但是能遮擋住人的一切氣息甚至命燈,算是燃犀油的升級版。
程星河又是搖頭又是咂嘴,意思是這家人真是錢多了燒的。
進到了豢龍堂,一擡頭,嚯,滿坑滿谷,全是龍。
彩頂上是九街搶珠,牆上是萬龍出海,桌子椅子上,都是小小的龍頭盤尾。
按理說,這在以前,是皇帝特有的殊榮,可因為他們家這豢龍氏的身份,應該是獨有一份特權。
不過,我倒是注意到了,在這裡出現的龍,無一例外,全是四爪和三爪。
而這偌大的地方,竟然就隻有水蛇腰和柔弱無骨這倆男人,顯得異常空曠。
水蛇腰叫董乘風,柔弱無骨那個叫董乘雷,董乘風老跟别人欠他幾百塊錢似得,耷拉着臉,歲數稍小,董乘雷倒是笑臉迎人,雖然笑的讓人不舒服,歲數比董乘風大一點,應該是兄弟倆。
而且,他們背過去的時候一說話,我就有了熟悉的感覺了——預知夢裡說什麼黑白髓的,應該就是這兩個人。
我四下裡一看,四處都沒人,試探着就問,這裡就他們兄弟兩個人?
董乘風回頭說道:“管你什麼事兒?”
董乘雷則拉住了董乘風,答道:“都忙。”
果然,這一路上非但沒有女人,男人都少見。
程星河低聲說道:“這地方是是不适合女人,彌漫着一股宮寒的感覺。”
白藿香透過鼋的裙邊皮白了他一眼,覺着他班門弄斧。
而且,越往裡走,我越有一種感覺,好像身後有人跟着我們似得,脖頸子上汗毛直立。
終于,到了一個内堂,内堂前面有一道很大的屏風。
這屏風年頭肯定也不短了,上面繡的是飛龍在天。
隔着屏風牙黃的厚絹面,我們看見裡面是坐着一個人,不過那人模模糊糊的身體輪廓上看,他圍着一條被子,好像身體不好。
董乘雷過去,把我們的來意說了一遍:“伯祖,您看現在怎麼辦?”
那個伯祖沒吭聲,程星河試試探探想過去:“老爺子是不是着了?”
讓我給拉回來了。
說實話,我心裡也挺緊張的。
而這一瞬,一個指甲撓玻璃似得聲音就響了起來:“我看看……”
這個聲音極為幹枯嘶啞,聽的人直起雞皮疙瘩,就好像,幾十年沒開口說過話了一樣。
董乘雷對着伸手,我也就把潇湘的那片龍鱗給拿出來了。
董乘雷雙手捧着龍鱗,小心翼翼的進去了。
我看着那個伯祖接過了龍鱗,身子忽然猛地顫了一下。
緊接着,他嘶啞的聲音再次響了起來:“這是從哪裡拿來的?”
他嗓子一使勁兒,簡直鑽耳朵的難聽!
我自然留了心眼兒,不可能白把潇湘的身份說出來:“您隻說,能救不能?”
伯祖沉默了一下,緩緩說道:“能。”
這一瞬,我的心猛地就跳了起來,潇湘這下,真的能回來了?
程星河也高興了起來,用肩膀撞了我一下:“你小子還真等到這個狗屎運了!”
赤玲也抱緊了我的胳膊:“爹,你為麼子這樣高興,是不是,是不是我媽要回來了?”
我一轉臉要跟赤玲說話,餘光正好看向了白藿香,發現她卻怔了一下,像是正在出神。
但是接觸到了我的視線,她很用力的露出了一個笑容:“真好。”
接着,就轉過了臉,像是不想讓我看到她的表情。
我吸了口氣,就看向了伯祖:“那,什麼時候?”
那嘶啞的聲音回答道:“過三天——三天之後,才有滿月。”
三天——已經等了這麼久了,三天而已,能等。
而那個嘶啞的聲音卻接着說道:“那,寒月呢?”
我答道:“您放心吧,董寒月我照顧的好好的,隻要我的龍回來,我立刻叫人把她送回來。”
站在伯祖身邊的董乘雷彎下腰跟伯祖咕叽了幾句,擡起頭來,這才說道:“你說你把寒月照顧得好好的,有證據沒有?”
證據簡單啊,我就拿手機要給啞巴蘭他們去個電話,可誰知道,手機的屏幕一亮,信号欄是空的。
對了,有陣法的地方,一般都沒有信号。
我一尋思,就把懷裡的那片龍篦子給拿出來了:“這個,算嗎?”
這東西是個真貨,他們自然都認識。
果然,他們的視線一觸到了那個金篦子上,頓時都直了眼,董乘風甚至倏然往前一撲,想把金篦子給搶到手裡!
我立馬就覺出不對勁兒來了——怎麼好像,比起董寒月來,他們更重視的,是這個龍篦子?
我翻身就讓了過去,躲避董乘風的能耐我還是有的,但讓我萬萬沒想到的是——董乘風的身子一擺,并沒有跟我預料之中的一樣翻轉,卻跟一道繩子一樣,纏到了我身上!
那是人類基本達不到的角度!
他人還在我面前,冰冷的,帶着淡淡腥氣的味道,卻繞到了我腦後!
這一下吃驚不小,而與此同時,另一個身影忽然出現,一下擋在了我面前:“你敢傷我爹,活的不耐煩了莫!”
赤玲!
她一把抓住了董乘風的手往下一扯,董乘風也沒想到半路殺出個程咬金,反手拽開了赤玲的手,赤玲手一揚,幾個屍油小鬼對着董乘風張牙舞爪就撲過去了。
四十二人油!
要是把董乘風弄死我手底下,就更麻煩了,我當機立斷,力道也就沒怎麼控制,誅邪手一炸:“赤玲,把東西給收回去!”
董乘風颀長的身體瞬間飛出去了老遠,重重的撞在了一個梁柱上,啪的一下,就把一隻龍爪給砸了下來。
赤玲不太情願,可也隻好把四十二人油收了回去,冷冷瞪着董乘風。
我自然也把龍篦子收回來了:“等你們把我的龍給治好了,我一定完璧歸趙。”
董乘風這一下抓了個空,不由十分失望,掙紮起來,還想搶一步,可董乘雷咳嗽了一聲,董乘風這才不情不願的垂手立在了一邊。
董乘雷笑吟吟的走過來,說道:“我這個弟弟年輕氣盛不懂事兒,看見了妹妹的東西,一時激動,請你不要跟他一般見識。”
我點了點頭:“不要緊。”
程星河低聲說道:“這叫一時激動,都要吃人了!”
董乘雷接着就說道:“那就請在寒舍逗留幾天——三天一到,伯祖肯定幫你救龍。”
我也就答應了下來,跟着董乘雷去落腳地。
可臨走的時候,我忍不住回頭,又看了那個屏風裡的伯祖一眼,這一眼不要緊,那伯祖的兩隻眼睛睜開,竟然泛起了兩點紅光。
我心裡一緊——好像,兩盞紅燈一樣。
但馬上,那兩點紅光就消失了,速度快的好像幻覺一樣。
董乘雷拉了我一下:“貴客有事兒?”
紅光沒了,說了也不會有人信,我隻好搖搖頭。
白藿香說得對,我們是為了潇湘來的,不能多管閑事兒。
可惜,後來我才知道——有些閑事兒,不是不想插手,就能不被卷進去的。
到了内宅,發現是個小小的青石院子,院子裡也有個荷塘,年代雖然久遠,但是十分幹淨。
董乘雷把我們安頓好了,低聲說道:“幾位住下,除了這兩個女人不能脫下鼋裙衣之外,還有一個規矩,請一定記住。”
“你說。”
“這幾天晚上,不管聽到什麼動靜,還請千萬不要開門——這對大家都好。”
啥意思?
可董乘雷顯然并不願意細說,隻是千叮咛萬囑咐,讓我們一定記住了。
等他走了,白藿香忽然拉住了我:“不好了。”
我一愣:“怎麼了?”
她轉手就往赤玲身上指了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