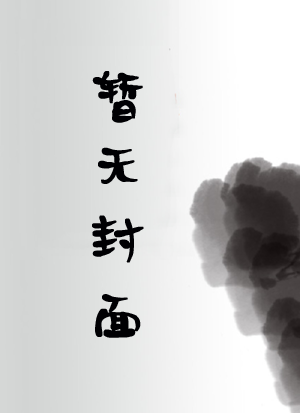當時我就長了個心眼,這東西反正在海裡也不要錢,不拿白不拿。
我就塞給了程星河,說你就當是大力水手吃的菠菜吧。
程星河弄清楚之後有些将信将疑,小心翼翼吃了一點跟怕我毒死他一樣:“不瞞你說,我這個人體質容易過敏……”
你放屁,你小時候翻垃圾桶的時候怎麼沒過敏?
我就跟他制定計劃,等下了水,先不要打草驚蛇,把海生給找到,再一舉把那幫弄傷蘇尋的給搞定。
程星河翻了個白眼:“我跟閣下無冤無仇,閣下為何要把我當成傻子?”
剛要動身,白藿香忽然跟想起來了什麼似得,站了起來:“你們等會兒!先把鞋脫了。”
啥?
程星河不耐煩:“我沒腳氣,你給七星看。”
老子也沒有。
白藿香蹲下就往我們光腳上撒了幾個蟲子:“幫你們動動手腳。”
對了,這海羅刹跟人的區别,除了他們的血是綠色的,那就是手腳跟人不一樣——他們普遍六個指頭,指甲很尖。
小蜇皮子大蜇皮子往身上一招呼,我們的手腳很快也跟沙灘上的腳印子一樣,成了尖銳的箭頭狀,模樣還挺唬人。
幾個路過的看見了,還以為我們是異形,躍躍欲試的在一邊想拿手機拍我們,被夏明遠趕雞一樣趕走了。
白藿香滿意的看着自己的作品,跟我們點了點頭:“快去快回,我們等着你們。”
我點了點頭,帶着程星河就奔着那個榕樹過去了。
東邊還真有一個特别大的榕樹,不知道多少年了,垂着發達的氣根,周圍都是綠茵茵的青苔,宛如一個年過耄耋卻精神矍铄的老人。
之前我還有點納悶,海羅刹的位置離着這麼近,我之前怎麼沒看出來,還往山上跑了一趟,這一瞅不要緊,原來那個榕樹前面有個小祠堂,正好擋在樹前面,神氣雖然不怎麼大,可卻正好把青氣給掩蓋住。
那個祠堂造型也倒是十分小巧,看上去很有文化底蘊,不過最近這些年估摸着香火很稀,漢白玉的台階上,也落滿灰塵,長滿了青苔。
這地方可以,隐蔽性挺高。
程星河跟我一甩下巴,我就看見了,這地方空氣潮濕,四處都被青苔給籠罩,唯獨一個地方沒長青苔。
樹的背面。
不長青苔,就說明時常有人觸碰。
我們倆奔着那個位置就過去了。
果然,敲了兩下,是空聲。
隻是,那地方不是普通的門,也沒把手縫隙什麼的,不知道怎麼進去。
我一研究,就看出這地方有一個凹槽,上面還沾着一些綠色粘液——海羅刹的血!
我立馬就把白藿香僞造出來的爪子伸過去了——别說,還真合适。
這一下,就聽見裡面咯吱一聲機擴聲,那塊樹皮跟電梯門一樣,緩緩就打開了!
往底下一看,一汪黑水。
我直接就跳下去了。
下面像是的水綠的發黑,像是深的沒有底。
被體重激起來的水泡飛快的往上一升,眼前一清明,簡直别有洞天!
數不清的彩色小魚成群結隊,頭頂飄蕩着植物的根系,深綠淺綠的水草随着水波飄搖,青翠可愛。
那幫天殺的海羅刹在這種環境生活,日子很滋潤嘛。
可惜你們動了我的人,那你們也就滋潤到頭了。
含了避水珠之後,在外頭倒是感覺很幹燥,這一進來,就跟幹了的植物吸到了水一樣,百八十個汗毛眼都打開了,渾身清爽,别提多舒服了。
我直接在裡面遊了一圈,這才反應過來程狗好像沒下來,擡頭一瞅,隻見這貨跟怕水燙腳似得,戰戰兢兢在上頭伸了半天腳指頭也沒下定決心。
我一頭沖出去,撸下了滿臉的水:“泥等勒劈呢?”
嘴裡喊着避水丸,說話不清楚。
程星河臉色煞白:“七星啊七星,你這“菠菜”行不行啊?你說萬一不管用,我……”
我急着給蘇尋出氣,也沒等他磨叽,往上一竄,來了個“蛟龍出海”,騰水而起,抓住了他的腳脖子,就把他給拽下來了。
程星河一下了水,表情别提多扭曲了,張嘴想喊,又怕喊出來被水嗆死,立馬捂住了自己的嘴,想往上蹬。
我一把将他拽下來,順帶把他的手他也拉下來了。
他那眼神驚恐的跟被人謀殺一樣,但很快,也反應過來了,難以置信的盯着面前的水,連翻了好幾個跟頭,回頭就瞅着我:“這菠菜多少錢一捆?”
捆你大爺!
我跟他比劃了一下,這玩意兒是有時效的,到點就得繼續吃,否則就得淹死你。
程星河一聽,立馬抱緊了水靈芝草的罐子,剛想說話,我們就聽到了身後猛地響起了一個聲音:“你們兩個哪兒來的?”
我一回頭,就看見了一個男人立在我們身後,手裡拿着個大叉子。
程星河自言自語:“閏土?”
他要是閏土,你就是猹。
看清楚了,那個男人孔武有力,目測二米出頭,一身虬結的肌肉,趕得上打虎客。
但是模樣就很難看了,一腦袋大瘤子,仿佛喀斯特地貌的模型。
對了,這羅刹素來是男醜女美,估摸着海羅刹也是一樣。
打蘇尋的,有這貨嗎?
程星河轉手要把狗血紅繩抽出來,我摁住他,因為避水珠的緣故不好張嘴,一甩下巴意思讓他問清楚了再說。
仇要報,但是罪不及族人,我們也不會濫傷無辜。
程星河會意,仗着吃了水靈芝草能随便說話,對那個喀斯特點了點頭:“大哥,今兒在外頭打死了個活人麼,真是威武雄壯,佩服佩服,都說喝了活人血壯陽,我們倆打算要點洞房的時候用。”
真的壯陽嗎?
那個喀斯特羅刹一聽,當時就一跺腳:“媽媽的,是聽說打死了個活人,可老子還沒分一杯羹,什麼時候輪到你們這些後生仔,哪兒有便宜往哪兒鑽,一邊涼快涼快去,都是撒币。”
說着,憤憤然就要趕我們。
這人說話本地口音,一股子蛏子味兒。
而且,好像挺暴躁的,活脫脫胡椒通投胎。
程星河打蛇随棍上:“哎呀,那一百二十個貨也太不是東西了,有那好事兒,竟然沒把大哥你叫上?狗眼看人低!”
喀斯特羅刹聽了這話受用,大瘤子摞着小瘤子的臉上才露出了幾分笑模樣:“你模樣長得醜,眼神倒是挺靈。”
程星河雖然又摳又貧,但是長相還是很好的,看來這海羅刹審美跟地上不一樣,以醜為帥。
而喀斯特羅刹掃了我們倆兩眼,有了點優越感,打開了話匣子:“實話告訴你們,是田八郎那夥人幹的,而且,嘿嘿,他們遇上了硬茬,折了七八十個弟兄,都是撒币。”
真兇叫田八郎?
得咧,狐狸眼,來收人吧。
程星河立馬問道:“那,上哪兒去找田八郎?”
喀斯特羅刹皺起了眉頭:“你們連田八郎都不認識?都是撒币!難道外地來的?”
程星河立馬點頭:“以前少小離家在廣州混,這最近都流行逃離北上廣,我們就回家鄉發展了。”
喀斯特羅刹看着我們倆,憐憫的搖搖頭:“看你們倆這模樣,也知道在外面混不出什麼名堂,回來了在家鄉好好幹,早晚能娶上老婆。”
娶毛線的老婆,我一聽越扯越遠了,就跟程星河擠眼。
喀斯特羅刹看我一個勁擠眼,懷疑我得了眼病,離着我遠了一點,像是怕傳染。
程星河連忙接着問:“那田八郎……”
喀斯特羅刹眼珠子一轉,奔着裡面一指:“一直往前,看見黃石頭往裡一拐就到了,不過我勸你們一句,最近不知道田八郎肚子裡裝了什麼花花腸子,老是召了一幫人在家裡叽叽喳喳,不大正常,媽媽的,都是撒币。”
程星河很會套話,沒幾句就套出來了——原來這海羅刹在東海地位也算不錯,比上當然比不了蟠龍蜃龍,但比什麼海無常海姑子可是強得多了,勉強稱得上二線貴族。
加上本地管理者水妃神以前就是海羅刹女出身,這一陣子更是能在附近水域橫沖直撞。
田八郎就是一個海羅刹頭領,手下不少小弟,恨不得天天橫着走,不過前一陣子盛極必衰,好像得罪了要緊人物,被水妃神一番嚴懲,折了面子,也不出門了,天天不知道研究啥。
他們要抓海生,肯定有什麼貓膩。
于是我們跟喀斯特羅刹告别,奔着黃石頭就過去了,臨走,喀斯特羅刹還熱情的告訴我們,千萬不要盯着田八郎的臉看,否則田八郎肯定不客氣。
它臉有啥新鮮的嗎?
沉入更深的地方,陸陸續續又見到了幾個海羅刹,那幾個海羅刹看見我們的長相,都跟吓了一跳似得:“你看那倆,長得跟人似得——要不是手爪腳爪,我還真以為是人呢。”
“是啊,醜成這樣,傳宗接代是夠嗆了。”
你們倆好看,一個長了倆犄角,一個嘴巴往下耷拉,跟沙皮狗似得。
好不容易到了黃石頭那,我們就想找上門去救海生,一轉臉見到了黃石頭後面,都大吃一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