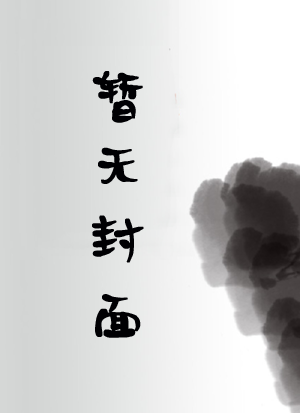啞巴蘭一愣,回頭就看我:“哥,怎麼啦?”
我沒看啞巴蘭,而是看向了蘇尋:“你當初看見白藿香放了酸梅,又對着酸梅射金針了是不是?”
蘇尋剛才聽啞巴蘭這麼一說,臉色瞬間就晦暗了下去,顯然十分受傷,但他還是梗着脖子,神色倔強,本來都準備好了被我們群起而攻之了。
而他一聽我開了口,頓時也愣了愣,擡頭看着我,重重的點了點頭:“我說過三次了。”
我接着說道:“那你就從另一個角度再說一次——我記得當時你走在白藿香前面,是怎麼看到白藿香放酸梅的?”
蘇尋沒想到我會這麼問,想了想,才回答道:“當時,我走着走着路,小蘭不小心踩到了我的鞋,我回頭一看,就看見白藿香在處理酸梅。”
越說這個,蘇尋臉色越不好看了,咬着牙,顯然一臉委屈,但還是梗着脖子,一副清者自清的樣子。
小蘭……還新一呢。
啞巴蘭倒是撓了撓腦瓜皮:“我踩過嗎?我怎麼不記得了?”
我沒回答,接着就看蘇尋:“你把白藿香給弄醒了,我問她兩句。”
蘇尋顯然不太樂意,像是怕白藿香從地上來個旱地拔蔥,把我給剝了一樣。
但我開了口,他還是照着我說的,捏在了白藿香脖子一個穴位上。
我剛才也看出來了,白藿香本來就是被蘇尋給弄暈的,肯定是血流不暢,通過那個穴位疏通開就行了。
果然,不長時間,白藿香皺起了眉頭,醒了一看自己在蘇尋身邊,立刻就着急了,我連忙讓她冷靜點,接着問道:“你之前說,我攔着廟鬼的時候,是蘇尋弄壞了木闆,導緻咱們幾個差點掉下去摔死是不是?”
白藿香立刻點頭,死死盯着蘇尋:“他肯定有問題!”
蘇尋嘴角一抽,倔強的看向了别處。
我接着問道:“當時亂哄哄的,你是怎麼看見的?”
白藿香一皺眉頭,也覺得我這話問的無厘頭:“怎麼看見的,用眼睛看見的呗!”
我接着說道:“你好好想想,當時那麼亂,你不關心廟鬼是不是會吃人,為什麼反而去看蘇尋?”
白藿香眨了眨眼,想了想,這才說道:“我本來是一直在看你,不,”她臉瞬間一紅:“我本來一直是在看廟鬼,但是不知道誰撞了我一下,我腳底下一踉跄,就看見蘇尋不對勁兒,木闆肯定是他動了手腳。”
蘇尋一聽,立刻擡起了頭:“我當時就是聽見了木頭有動靜,怕塌陷下去,才查看木頭的糟朽情況的。”
白藿香瞪着蘇尋,還是劍拔弩張的:“平時話那麼少,原來留着狡辯的時候用呢?”
被人撞了一下啊。
程星河已經聽出不對勁兒來了:“七星,你是不是弄清楚什麼了?”
差不多,但還有一點。
我看着白藿香,接着又問道:“還有一件事兒,你是不是在我口袋裡放過一個玉簪子?”
白藿香一愣,臉色微微就紅了:“我沒放過。”
跟白藿香在一起這麼長時間,知道她很好猜透。
她撒謊的時候,有個特點,就是一定會轉開臉,不去看你的眼睛。
現在就在撒謊。
而就在這個時候,我們全聽見了一陣“嘩啦啦”的聲音。
當然,這不是那些紙人,而是地上的沙粒碎石——都沖着一側滾了過去。
與此同時,我們也覺出來,腳底下開始震顫——整個塔傾斜的越來越厲害,眼瞅着要倒了。
啞巴蘭連忙說道:“哥,你這些問題都太無厘頭了,這塔可是快塌了,眼看着罪魁禍首就在咱們眼前,倒是……”
程星河也怕死,但是他信得過我,就把啞巴蘭的肩膀給摁住了:“你着什麼急啊,你還不知道七星,他問話,肯定有他的道理,小孩子懂個屁。”
不過程星河也還是偷偷踹了我一腳:“這個環境不适合裝逼,我勸你速戰速決,我可不想現在就下去找我爹。”
我則盯着也開始緊張的白藿香:“是誰給你的?”
白藿香咬了咬牙,這才說道:“是……是啞巴蘭給我的。”
這話一出口,程星河一下就愣住了,轉臉看着啞巴蘭:“你啥意思啊,不是,你要脫單,也得明白兔子不吃窩邊草的道理吧?”
啞巴蘭連連擺手:“藿香姐,你這話怎麼說的,我什麼時候給你簪子了?”
接着啞巴蘭求助似得看着我:“哥,你說是不是這個邪祟狗急跳牆,要往我身上潑髒水,挑撥離間啊?”
白藿香一聽這話也變了臉色,像是下定了決心,這才說道:“是,是在廟鬼那的時候,啞巴蘭說那個東西是他在家裡拿的護身符,在危險的時候,能保平安的,才給了我一個,我……”
她紅了臉,沒有說下去。
我明白了。
她是擔心我,所以在我背着她過“愛”那一層的時候,偷偷把那個“護身符”放在了我身上。
她不知道那東西,會招來“愛”那一層的執念鬼。
程星河也聽出不對勁兒來了,盯着啞巴蘭:“怎麼回事?啞巴蘭,你有好東西,怎麼沒想着我們?酒足飯飽勾二嫂,你小子什麼時候這麼沒節操了?”
嘴裡說着,程星河的手伸到了後腰——是他動手之前的習慣性動作,要抽狗血紅繩了。
蘇尋也死死的盯着啞巴蘭,像是不相信自己眼睛一樣:“難不成……”
啞巴蘭呼吸立刻急促了起來,連連擺手:“不是不是,哥,你别聽他們胡說八道,這明明就是這裡的鎮物挑撥離間,就是要破壞咱們之間的信任,讓咱們自相殘殺啊——哥,你不記得進門的時候,那兩個自相殘殺工匠兄弟了?你,你可千萬不要中計,步了他們的後塵!”
我看着啞巴蘭,平淡的說道:“白藿香和洞仔我問完了,現在我問你——你是怎麼知道蘇尋懷裡有東西的?”
啞巴蘭一愣:“這,這不是明擺着的嗎?哥你肯定也看見了——程二傻子也看見了啊!”
我答道:“我會望氣,是看見佛光了,程二傻子有二郎眼,也比别人看見的東西多,可啞巴蘭你既不會望氣,也沒有二郎眼,是怎麼知道蘇尋懷裡有東西的?”
從外面看,可看不出來——忽視掉蘇尋胸口的佛光,他的衣服穿的妥妥帖帖的,根本就不像是藏了東西的樣子,就算藏,也最多放個核桃之類的。
啞巴蘭吸了口氣,努力想證明自己:“靈骨也不大,從外面看不明顯,也很正常啊,我就是看見,他胸口像是放着個什麼東西……”
我知道蘇尋胸口的口袋是常年放着個東西,一個小方盒子。
可我接着對啞巴蘭就笑了:“對,你說出這話來,那就敞亮了——我再問你最後一句,你怎麼知道靈骨不大的?你見過?”
啞巴蘭的臉色徹底變了。
我們進來的時候,就看見了很多沒有舌頭的肉身坐化佛。
所以,我們在腦子裡面,自動就覺得,寶頂上供奉的大法師靈骨,也肯定是個肉身坐化佛。
沒進塔的時候,啞巴蘭還嘀咕了一句,到時候把大法師的肉身佛取下來的時候,他勁兒大,負責扛着。
可怎麼一進了塔裡,你就知道“靈骨不大”,甚至能藏在人身上?
我看着他就笑:“這麼說來,還是我們想錯了——原來靈骨,是舍利子啊?啞巴蘭?”
啞巴蘭的表情徹底變了,那個愣頭愣腦的表情,冷不丁就眉尾上揚,嘴角斜勾,是啞巴蘭自己從來沒出現過的表情。
凜冽而又鋒芒畢露。
白藿香和蘇尋一下也全愣住了。
他微微一笑,帶着點居高臨下的倨傲看着我:“你不是一般人。”
實不相瞞,我要是一般人,已經死了八百回了。
之前的一切都解釋的桶了——難怪江采萍剛要說出真相的時候,他出來把江采萍打退,難怪江采萍一看見他,就要躲起來。
我當時就覺得奇怪,江采萍能凝結成實體,能力不在煞之下,為什麼怕一個玄階的啞巴蘭?
他怕是存了心思,連江采萍也要滅口——倒是幸虧江采萍跑得快。
更别說,甩開了程星河,跟我們一起上塔,搬起了壓怨石的是他,被紙劃破了,用血腥氣引過紙人的,也是他。
一開始我就覺得奇怪,這遮婆那既然能讓人挑撥離間,心計自然很深,絕對是不會把自己給暴露出來的——而白藿香和蘇尋,一進了塔裡,就成了頭号嫌疑人。
真的遮婆那要是潛伏在了我們身邊,怎麼可能讓自己粘上這種嫌疑?
所以那會兒我就覺得,她們倆隻是煙霧彈,真的遮婆那,不可能在她們倆身上。
而他确實沒讓我失望,隐藏的确實不錯,我一開始都沒找到疑點——他出的唯一一個纰漏,就是他太着急了。
我也對他笑了笑,壓在他肩膀上的手一下用了力氣:“我也有說錯的時候——不應該跟你叫啞巴蘭了,現在我應該跟你叫,遮婆那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