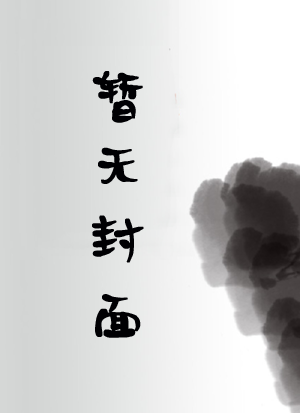她也一直記得,這是我媽跟我約好的日子。
我點了點頭:“謝謝。”
她幫我整理好了衣領和袖口,對我一笑:“祝你一切順利——不過,還有一件事兒。”
“什麼?”
“哪怕是去見你媽,安全起見,你必須用蜇皮子換個臉。”
不能用真實面目去見我媽?
這确實讓人失望,可是這話也對——我自己已經陷入這麼大的麻煩裡了,不能把我媽拉下去,否則……
想起了那個夢,我心裡倏然一沉。
“行。”
蜇皮子在臉上咬來咬去,我雖然平時最怕疼,但是今天心裡有事兒,所以一直沒感覺出來。
白藿香覺察出來了:“你今天,好像心事重重的。”
關于我的事情,全瞞不過她。
我有點不好意思的點了點頭,這一點頭,一個蜇皮子蜇到了嘴角,我就吸了口涼氣。
終于能解開一個心結,應該是人生一個轉折,有期待,可做了那個預知夢,也有擔心。
“你說,見到了她,第一句話怎麼說。”
不能一開口就叫媽——總覺得過于唐突了。
可不叫媽,叫什麼?
我平時不是磨磨唧唧的人,可這件事兒對我來說,很重要。
白藿香一笑,捏了捏我的額頭調整形狀:“順其自然。”
也對。
是有點過于燒包了。
白藿香做完了臉,端詳了一下,十分滿意:“有點羨慕你。”
“嗯?”
“至少你還能見到你媽。”
對了,白藿香她媽在她沒記事兒的時候,就沒了。
“你要是羨慕,那也沒什麼。”程星河已經打着哈欠出來了,一邊百無聊賴的掏耳朵,一邊說道:“七星有了媽,你也拿着七星他媽當媽就行了。”
白藿香的臉頓時跟個燒開的水壺一樣,瞬間燒紅:“你又饞一日喪命散了是不是?”
說着,一把針跟天女散花似得,對着程星河就落下來了。
程星河敏捷的把身子翻過去:“不是,你急什麼眼?我沒别的意思——讓你認個幹媽。”
這段時間,你可沒少從白藿香這裡受訓,身上功夫進步了不少。
白藿香一怔,随即意識到這一發作更顯得心虛,索性大怒,幾個蜇皮子奔着程星河也飛了過去,把他的鼻子蜇的跟駝峰似的,捂着慘叫。
我把衣服換上,挺像那麼回事兒——起碼,不丢人。
很多歲數大的,都挺喜歡我的。
一出客廳門口,我一愣,院子裡面,已經坐了不少人。
師父,老四,啞巴蘭,蘇尋,老亓,還有那些湊熱鬧的靈物。
齊齊整整的。
“恭喜門主。”師父沖我一笑:“要把咱們厭勝的那位夫人接來了。”
接不接來,還不好說。
我媽身份大貴,這些年,過的一定很好,不一定會為了我改變自己的生活。
“你去了,一定把二十年前的事情,全問清楚,”老四站起來,氣勢洶洶:“老二,當年到底是怎麼回事。”
我點了點頭:“放心。”
這件事情的重要性,僅次于見她。
“哥,一路順順利利。”啞巴蘭給我比了個心:“等你回來,一起團圓。”
蘇尋也在後面點頭。
靈物們則争先恐後往上送東西:“這個萬壽緞送給老婦人——陰山巧蠶織造出來的,冬暖夏涼!”
“這個樂眠席還請笑納——三川邊的蘆葦編的,睡在上頭,騰雲駕霧一樣,隻做好夢!”
我連忙擺了擺手:“去見我媽,又不是去擺攤,不拿不拿——真要是能順利把當年的事情弄清楚,再收禮不遲。”
一開始靈物們覺得很掃興,但是一聽也有道理,隻好收起來了:“那,下次一定!”
“一定!”老亓已經替我給收下了。
星星逐漸隐沒,東方泛起了魚肚白,天馬上就要亮了。
我跟他們擺了擺手,鑽到了水母皮底下。
雖然是私事,可四相局小分隊的的幾個人都想跟着。
程星河和白藿香幾輪剪刀石頭布之後險勝,趾高氣揚的跟我一起鑽到了水母皮底下。
剛要出門,白藿香忽然叫住了我。
我回頭,她趕過來,認真的說道:“你可以善良寬仁,但一定得要在護住自己的前提下。”
我點了點頭:“記住了。”
程星河金刀立馬跨上了電動,車把一擰,來了句戲腔:“白馬銀槍似天神,馬到之處人頭滾……七星,爹像不像趙子龍?”
“像科莫多龍。電充足了嗎?”
“廢話。”
電動車一騎絕塵。
清晨的風穿透了水母皮,涼如水,天上還挂着一彎殘月。
街邊的梧桐樹掉了滿街的葉子,銀杏一片金黃,不知道為什麼,秋日裡,總是讓人感覺格外凄涼。
又一個夏天将一去不回。
“七星,你說最近江辰怎麼樣了?”
“你想他了?”
“我想他幹什麼?我隻是覺得,這孫子總是個心腹大患——他沒死,就不踏實。”
真要是那麼容易死,還叫什麼江真龍?
江辰幹了不少壞事兒,但是一直沒受到大制裁,除了江辰背後關系硬,應該還有一個原因,就是天師府跟江家的目的一緻——保局。
天師府要保三界平安,江家要靠着四相局改局出真龍,雖然理由不同,但殊途同歸,所以應該是合作的關系,天師府看中江家手裡關于四相局的一切資料,江家背靠大樹好乘涼,不會真的撕破臉。
而且,天師府招攬這麼多武先生一起來,到底是搞什麼呢?
可惜現在成了過街老鼠,沒法查清楚。
車到了地方——這地方真荒,四周圍是很多的黃花斛木,秋天是結果子的季節,一片苦香氣。
中間有口井。
這地方很慌敗,以前還有一些殘垣斷壁,據說是個有錢人家的園子,立了好幾百年。
但是後來那戶人家開始鬧鬼,一開始死妾,後來死正妻,最後老太太也不行了,找人一看,說他們家陰陽失衡,井裡有怨氣。
原來一開始,是因為老爺買了個妾,極盡寵愛,夫人嫉妒,叫妾看花,其實把妾推進個平時不用的井裡了,對外說妾跟馬倌跑了。
自此以後,家裡就不太平,先生一看,說好麼,這是出了井魔了——原來幾百年了,每隔一段時間就有女人被推下來,井裡的東西吃了這麼多人,煞氣越來越重,胃口越來越大,你不投喂,她就爬上來自己開葷。
後來井口填上,卻總自己開,人還是照樣的死,那家人不敢在這裡住着,就跑了,園子荒廢了,有人想要這塊地,可一跟井沾邊,總是沒好事兒,時間長了,傳說越來越厲害,說到了現在,這井裡還有東西,會伸胳膊往外爬,所以這地方一直都沒人來,我媽選地方選的很不錯。
煞氣是不小,不過沒有在我們面前造次。
我下了電動車,揉了揉坐麻了的屁股,觸景生情想起來了:“程狗,你現在還有二郎眼嗎?”
程星河答道:“時靈時不靈的——跟接觸不良一樣,不過能看見東西就算是不錯了,找到了機會,你給點個穴,把我們家祖先,重新葬在了個利眼睛的地方。”
“好說。”
啞巴蘭他們家好像也要遷墳了。
到時候,一起看看。
從早上等到了中午,一直也沒看見我媽的蹤迹。
程星河已經吃了兩盒自熱米飯,終于不耐煩了:“你媽還來不來了?沒準想開了,又不要你了。”
“催什麼?我媽可能有事兒。”
上次我讓她白等了一天,這次等等她也沒什麼,我就跟程星河說,你着急就先走。
程星河很不服氣的撇嘴,罵我媽寶男。
那也比沒媽男強。
正說着呢,忽然程星河把自熱米飯的盒子一蓋:“有東西來了。”
你這眼睛不是挺好使嘛?
順着他的視線一看,我就看見,一棵很大的黃花斛木後面,出現了幾團子黑影子,像是正在窺伺着我們。
我頓時皺起了眉頭,是妖氣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