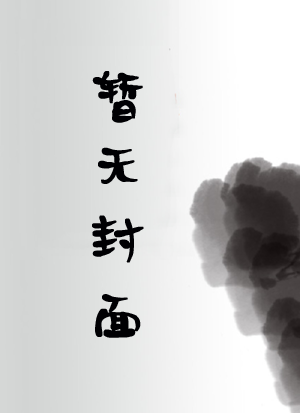是聽說靠山很厲害,但我還真不知道。
程星河一隻手指了指上頭:“那邊的人——據說,跟你老婆是同事。”
我心裡一提——吃香火的?
不是,吃香火的怎麼摻和上了人間的事兒了,還在人間有産業?
“哪一位?”
“小道消息,說正是主宰生死的。”
那不正是頂頭的父母神?
消息要是真的,那還真是得罪不起。
不是,這事兒我是冤枉的啊,我一尋思,就指着韓棟梁和邸紅眼:“你們給我做個證去。”
那天我先進了回龍鐘裡,後來二姑娘來了,再後來,邸紅眼他們也闖進來了,還有齊鵬舉。
不過,後來齊鵬舉被二姑娘碎了手腕之後就不見了,估摸着是心理承受能力不行,受不了老齊家再一次丢人,先離開了。
邸紅眼有些為難,支支吾吾大舌頭的說道:“嗚嗚……”
音調能勉強辨認出來,說的是(“我們倒是想,可郭洋被打的時候,我們參加了砂山龍脈研讨會,好些人知道。”
啥?我一問時間——好麼,離着郭洋被打,已經過去三天了,我還以為隻過去一天呢!
對了,人被困在陣裡的時候,對時間的感覺,跟外面也是有差距的,可能我進去之後第二天,二姑娘才進去,第三天,邸紅眼等人也誤闖進去了。
那我就更沒有人證了。
不管怎麼着,這誤會得趕緊解釋清楚,誰想平白無故背黑鍋,面對的還是父母神。
一見我像是有急事兒,邸紅眼他們還有點高興,以為自己的事兒也就算了,我回頭就跟吳先生說:“麻煩您幫我盯牢了他們,我還有事兒跟這些人請教。”
武先生承蒙我幫他擋了鬼眼蛾的災禍,一口就答應了下來,邸紅眼他們的笑容也一下就僵住了。
這會兒天色已經從烏黑變為青藍,快亮了,我下樓的時候路過了一個窗戶,不經意,就看見了一顆星星,從南邊墜落了下來。
當時我心裡就咯噔了一聲。
這叫“飛星入南鬥”。
跟“刨墳出太歲”一樣,是最不祥的征兆之一,見者,一月之内,必有大災。
跟老怪物,還有皇甫球說的一樣。
程星河見我愣神,也要跟着看,被我眼疾手快把腦袋給推過去了,不由十分不滿:“你是不是看見流星了,不讓我許願?”
本地傳說,要是看見流星,倆人一起許願,那說得快的才會成真。
我說你懂個屁。
我如果沒學厭勝冊,那我就隻好瞪眼等倒黴了。
可現在我知道,飛星入南鬥其實是可以禳解的。
那就是以借運法,把這個災禍,轉移到了其他人的頭上。
可自己的災禍,抓别人擋槍,我也不是那種人。
算了,入行以來,大災小災繁如星鬥,不是都扛過來了嗎?這一次,一定也能扛過來。
這麼想着,我就帶着程星河他們下了樓。
不過這地方貌似也被高人指點過,按着流星趕穴法設置的,很容易走錯,程星河正要開一扇門呢,亓俊攔住了他,往另一側一指,這才豁然開朗。
程星河一樂:“欺君,你上廁所要是有認路這麼快就好了。”
鬧半天,他們一起進來找我的時候,他們差點因為亓俊上廁所時間太長而遇上麻煩。
亓俊不樂意提這個話題,假裝不知道。
我忍不住看向了亓俊:“這崇慶堂,是井馭龍他們從你手裡收購來的?”
亓俊一愣:“你怎麼……”
簡單,我來的時候,就看見了,崇慶堂附近,有一個下刃煞妨主局。
投射到主人身上的,除了損根基,那就是下不利。
一早就覺出了亓俊身上行氣不太對勁兒——他不像是天生的花架子。
這會兒一看,亓俊臉上的運勢也是不怎麼好,但是田宅宮上有紅氣,說明他還是這個地方的主人,不過大概隻是名義上的。
果然——那個妨主局,就是井馭龍布下的,但是下的很高明,亓俊沒有瞧出來,還照常做生意。
但是這以後,萬事不順,崇慶堂的生意一落千丈,又有了來自上頭的壓力,井馭龍可以說強買強賣,就把崇慶堂弄到手了——名義上還是亓俊的,一方面能繼續克制亓俊,一方面,他隻作為一個“過客”,就不會被下刃煞影響。
亓俊也不甘心,眼睜睜的看着崇慶堂從給先生行方便的市場,變成坑蒙拐騙的中心,誰願意自己的心血付之東流,就偷偷去查井馭龍,想看看有沒有希望把崇慶堂給奪回來,這就發現井馭龍殘害靈物的事兒了。
他動了憐憫之心,才救下了那些靈物。
後來,也因為籌措錢給靈物找容身之處,才跟我遇上了。
他擡頭就說道:“崇慶堂給你,我放心。”
我擺了擺手:“我不要。”
他沒明白:“不要?”
我點了點頭:“你等着吧,郭洋的事情解決清楚了,我把崇慶堂物歸原主——回到你手裡,我也放心。”
程星河正研究着崇慶堂值多少錢,使計算器噼裡啪啦的算着呢,一聽我這話,一下就傻了,計算機好險都沒掉地上:“七星,你說啥?不是,這到嘴的鴨子,你吐出去?”
亓俊也瞪了半天眼:“可是……”
可是,崇慶堂這麼大個産業,我這樣一場賭賭的也不容易,差點把命搭上,怎麼就輕輕松松物歸原主了?
我答道:“就跟遇上老怪物的,惡人有惡報一樣,我覺得,好人也應該有好報。”
比如,拿回屬于自己的東西。
亓俊的眼眶子一下就紅了,但他歪過頭不想讓我們看見。
我和程星河他們一對眼,程星河雖然不甘心,可也隻好裝成沒看見的樣子,咚咚咚往前走:“得了,啥也不說了,七星是個富貴命,這點東西,怕也看不進眼裡去。”
啞巴蘭也跟着應聲:“沒錯,我哥不缺這一鱗半爪。”
程星河已經撿起手機,看見崇慶堂的市值了,長長一串零,心疼的回頭給啞巴蘭腦袋上來了一下:“一鱗半爪——說你胖你就喘!”
啞巴蘭委屈的捂住腦袋:“不是你先說的嗎?”
我也往前走,可亓俊的聲音就在我身後響了起來:“李北鬥,以後有用的上不才的,開口。”
話并不華麗,但是,我聽得出真心。
我沒回頭,擡起手擺了擺:“現在還不敢當,事情成了再說!”
可亓俊的聲音很固執:“不管成不成——你的心意,不才記住了。”
“好說——替我給那些靈物帶個好。”
回商店街的路上,程星河一直不愛搭理我,隻顧着摁計算器——崇慶堂是拿不到手了,可他還是非得過過眼瘾,看看崇慶堂的利潤,看的直歎氣。
等快到了商店街,程星河才愛理不理的說道:“七星,你先做好了心理準備吧,銀莊的人,可都是刺頭。”
他們這一行,沒刺頭也開不起來。
果然,進了商店街,就看見黑壓壓的一片人,其他的鋪子全拉下了鐵拉門,生怕那些人暴起把自己的鋪子砸了。
靠近一看,白藿香和蘇尋在店堂裡站着,金毛和小白腳一邊一個,還有倆人各自坐在了鋪子前面的一對石獅子上,兩方對峙。
我一愣,兩方?
再一瞅,一方自然是郭洋——一身的紗布,腋下架着一個拐,好賽金字塔裡剛逃出來的法老。
另一方,馮桂芬?
這是我們這塊混道上的女老大,玄素尺就是從她家院子裡起出來的。
她一直拿着我當個恩人,對我不錯,不過我這一陣子一直沒在家,很久沒看見她了。
隻見她氣勢洶洶,在獅子腦袋上坐的端端正正的,身後都是她的馬仔。
我看得出來,她就算表面上氣勢洶洶,穿着菲拉格慕高跟鞋的腳,也微微顫抖。
我心裡不由一陣感動。
銀莊的人,哪怕是她也忌憚。
可為了給我撐腰,她還是來了。
郭洋閉着眼睛假寐——身後還立着個輸液架子,而他身後那個壯漢馬三鬥先看見了我,連忙捅了捅郭洋。
馬三鬥力氣奇大,一下就捅的郭洋滲了血,騰一下起來,就要罵他,可一看我來了,郭洋立馬扶了扶眼鏡,似笑非笑的說道:“李門主,你可算是回來啦!咱們的賬,也可以算一算了吧?”
這個陣仗……
不光白藿香和蘇尋松了口氣,馮桂芬回頭,也驚喜不已:“李大師,你可算回來了……你放心,有我馮桂芬在這,絕對不讓你吃虧!”
我隻好對郭洋說道:“我要說,那個人不是我,你信嗎?”
郭洋一愣,接着哈哈大笑——但是一笑扯了傷口,表情變的很猙獰,隻好收回笑意,冷冷的說道:“我信……”
這麼通情達理?
可還沒等我誇他,他就直勾勾盯着我:“信你也行,可除了你,還能有誰?除非,你有不在場的證據,拿出來給我看看也行。”
我上哪兒給你拿去?
馮桂芬一瞅我,就知道我拿不出來,罵道:“那你把李大師揍你的證據拿出來也行。”
郭洋冷笑着說道:“這麼說,李門主是想着跟我們銀莊翻臉了?也行。”
他跟後頭一擺手:“把這個門臉給砸幹淨了,人給揍了,免得傳出去,人人都覺得咱們銀莊是軟柿子,誰都能上去捏一把。”
我自然不想翻臉——一方面我不可能這麼被冤枉,一方面,我們的錢還在他們那呢!
沒等我說話,那個馬三鬥先過去,食指和拇指往門上一夾——跟拿餅幹一樣,就把我們的門給卸下來了半扇!
蘇尋見狀,過去就要還手,可啞巴蘭比他還快,上去就搶。
馬三鬥的力氣有目共睹,這啞巴蘭也不是吃素的——這倆人碰一起,那妥妥是一對綠巨人!
不光如此,隻聽“咣咣咣”,一陣顫動,遠遠一個龐然大物也出現了,這不是看上啞巴蘭那個肉山小姐嗎?
“小蘭,有人欺負你,你怎麼不說?”肉山小姐怒道:“我看看誰吃了熊心豹子膽,在我男朋友這撒野?”
啞巴蘭連忙擺手:“還不是男朋友!”
好家夥,這三對付在一起,那不是飛沙走石,得跟世界末日一樣?
馮桂芬呸了一聲:“好哇,先動手了是不是,都上,誰怕誰,一起熱鬧熱鬧!”
不好,商店街怕是都要保不住了。
古玩店老闆也不知道從哪裡鑽了出來,眼瞅着快哭出來了:“北鬥啊——你讓這幫高人收了神通吧,我們這小本生意,禁不起折騰啊!”
我也知道,可看郭洋這個樣子,不像是能善罷甘休的。
我剛要說話,一個聲音就從我身後響了起來:“郭先生,這事兒還沒查清楚,有人給李北鬥擔保,行不行?”
郭洋本來一臉怨怒,可一看我身後那人,表情悚然一動:“您——怎麼親自來了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