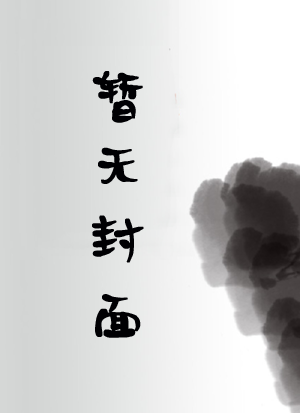她再次看向了我,眼神終于有了狐疑:“你為什麼這麼關心四相局?”
程星河往前搶了一步,又要把襯衫取下來:“你說不說吧?”
董寒月咬了咬牙,一臉的不甘心。
我知道,她其實是不服氣的,本來以她的本事,我還真不是她的對手。
可誰讓她有那種弱點呢?
也可以說我運氣好,不過,我赢得心安理得,運氣,本身也是能力的一環。
她這才咬了咬牙,說道:“據說,當年建造四相局的人花了很大的代價,才請到了我們那個先祖。先祖不辱使命,也确實幫助着修好了青龍局,但是後來,有人來了話,說四相局出事兒了,請我們家先祖再去一次,他那一去,就……再也沒有回來。”
出事兒——四相局,被人改過。
我立馬問道:“是誰請的?”
她答道:“說了你也不認識——江仲離。”
果然是江仲離。
把他們豢龍氏的祖先叫進真龍穴的時候,出了什麼事兒了?
改局的事兒,好像是個關鍵。
馬元秋,水百羽,甚至江辰身後的人,跟改局的事兒,是不是都有某種關聯?
而現在,知道真相的,應該也就是江辰和夏家仙師了。
他們去了長樂島,一時半會兒也找不到他,甚至——他們有可能先我一步,找到了真龍穴。
要是能從其他的地方知道真相,那就太好了。
我看向了董寒月,她為了井馭龍做到了這個份兒上,就是因為井馭龍答應幫他們去真龍穴找人?
“你告訴我,”我看着董寒月:“跟井馭龍接觸,許諾帶他去真龍穴的人,到底是什麼來曆?”
她瞳孔一縮,不由自主有了一絲懼意:“那一位,不是一般的人……”
“我知道,”我答道:“他叫江辰,是不是?他還常常自吹自擂,說自己是真龍轉世。”
董寒月沒有回答,顯然是默認了。
我接着說道:“你們既然是豢龍的家族,為什麼那麼畏懼他?你們不是他的克星嗎?”
董寒月擡起寒氣浸浸的眼眸:“那位,不是普通的龍——是最尊貴的一個,哪怕我們家,都不能動他。”
豢龍人,也有不敢動的龍?
我一愣:“最尊貴的?”
她微微點了點頭:“你要是跟他作對,那我可以保證,你絕對不會有什麼好下場。”
實不相瞞,我跟他作對時間不短了,我倒是想看看,他到底有多大的本事。
現在,能找到江辰的,也就那個井馭龍了。
我站起身來:“你不是已經通風報信兒,叫家裡人來找我算賬了嗎?那捎帶腳,再帶一句話,把井馭龍給我帶來。”
董寒月微微皺起眉頭:“你怎麼知道……”
“好說,這地方本來有八個傀儡,有四個是你送給井馭龍的,有四個是你這次自己帶來的吧?可現在,那些傀儡,隻剩下七個了。”我答道:“少了的那個,隻有你使喚的動。”
董寒月看向了我的眼神,終于變了變——終于知道,我比她想象的難對付。
程星河有點緊張:“七星,要是豢龍氏真來找你算賬,那……”
還是那句話,他來,我就等着。
我對董寒月笑了笑:“這一陣,先委屈你到我們家呆一陣,到時候,我會告訴你家裡人——一手交井馭龍,一手換你。”
董寒月一輩子可能沒讓人這麼拿捏過,一張慘白的臉泛了怒意:“你好大的膽子!”
是啊,我天生膽子就大——不靠着這個膽子,我活不到今天。
這個時候,田藻連忙拉住了我:“先生,你的事情都弄明白了,那,我們家老爺子……”
卧槽,剛才董寒月要弄死我們,偌大的屋子塌了一大半,四處都是磚石瓦礫,那些人臉藤和田宏德,已經被埋了起來,不知道被壓在了什麼地方。
我四下裡看了看,辨别出一個底朝天的純銅大相框下頭有青氣,趕緊就把那個大畫框給掀開了。
這一掀開,當時就倒抽了一口涼氣。
當時田宏德被束縛在人臉藤下面,動彈不得,董寒月一心殺我,下手極重,那個相框把他腦袋砸出了一個雞蛋大的窟窿,紅的白的都淌出來了,而他一雙空洞的眼睛,還仰望着塌陷的房頂後,露出的一方天空。
他臉上還是帶着希望的,可惜,他的希望終究是落空了。
飛星入南鬥的劫難,連積德行善攢功德的我都扛不住,更别說他了——真是聰明反被聰明誤。
田藻跑過來,怔怔的看着田宏德,忽然趴下就大哭了起來:“老爺子,你醒醒,你看看我啊!”
當然,田宏德再也動不了了。
而田藻剛一過去,數不清的枝條,跟活了一樣,對着田藻就纏。
田藻吓的屁滾尿流,連忙退到了後面——那些人臉都出現了淡淡的紅暈,“嘴角”也像是挂着了淡淡的笑意。
那些眼睛就更别提了,全是睜開的。
田藻大口喘氣,接着,回頭看向了董寒月,聲音帶着哭腔:“是你——是你把老爺子給害死的!”
董寒月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不說,還擔心井馭龍,哪兒還有心情搭理田藻。
田藻連個回應也得不到,就要上去擡手抓董寒月,可對上了董寒月冰冷的視線,懸在了半空上的手,一下就定格住了,他親眼看到了她的本事,就好像獅虎哪怕被關在籠子裡,也沒人敢把手伸進去一樣,他接着哀哀的哭了起來:“老爺子欸……你被這個女人好苦……”
是誰害死的田宏德?
财氣蟲娘娘的反噬,我的飛星入南鬥,還是董寒月那一記殺招?
不,都不是,害死他的,是他自己。
程星河咳嗽了一聲:“七星,現在怎麼辦?”
我答道:“還能怎麼辦,回家,等。”
等着豢龍氏,拿井馭龍來換人。
但是這個時候,我發現白藿香東張西望,就問她在看什麼?
她低聲說道:“你沒察覺,少了一個東西?”
對了——她這麼一說,我才想起來。
那個财氣蟲娘娘不見了!
程星河皺起眉頭:“不好,那東西不會再繼續害人吃骨髓吧?”
那東西在我後背上吃了癞蛤蟆的毒液,至少一個月之内,是沒有害人的能力的,而它元氣大傷,跑也跑不出多遠,我立馬就要把那個東西給找到,隻要燒掉了,就一了百了了。
田藻一聽我的意思,剛要點頭,就聽見了花園另一角,響起了一陣雞叫。
他們家豢養了非常漂亮的十色雞,也會打鳴。
是啊,天空東邊,出現了一層漂亮的黛青色,這雞飛狗跳的一夜過去,天要亮了。
田藻連忙說道:“已經耽誤了先生這麼長時間了,可不好意思再麻煩先生了,既然那個東西現在好抓,那就交給我吧——我們田家畢竟也是個大家族,這件事兒,越少人知道越好。”
這倒也是。
我就點了點頭,但是一看田藻臉上的氣色,心裡就清楚了幾分。
田藻一看我答應,立馬把臉上的污泥和淚水給抹了下來,給我安排了車,把我送走了,臨走的時候還說,雖然老爺子沒了,但是我弄清楚了财氣蟲娘娘的真相,是他們田家的恩人,該給的報酬,絕對不會手軟,下午三點就奉上。
我們也就把董寒月也帶回去了。
回頭看過去,那個一夜驚心動魄的地方,成了晨曦下的一片廢墟。
果然,回到了商店街,我的新手機就探出了一條新聞消息:“重磅新聞,超級富豪田宏德忽然離世,根據遺囑,侄子田藻(原名田一彪)繼承家業,成為田氏新任接班人,據可靠消息稱,田藻是個名不見經傳的旁支子弟,為何得天獨厚,讓我們……”
程星河掃了一眼,高興了起來:“這小子很有法子嘛!混上接班人了?那咱們的錢不用愁了,這一次沒白幹!”
我笑了笑——事兒沒這麼簡單。
财氣蟲娘娘之所以不見,果然是因為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