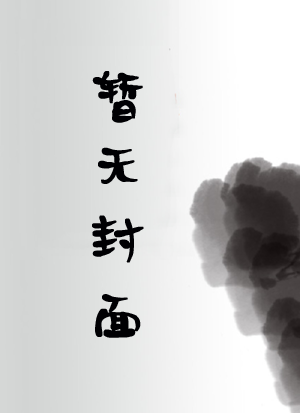我當機立斷,一下把身上的啞巴蘭甩了出去,與此同時,“啪”的一聲,那道青色的絲緞一樣的東西,奔着我就卷過來了,跟啞巴蘭隻差一指,擦身而過。
那東西帶在了我身後一個“胭脂原料”上,“噗”的一個悶響,那個塊頭挺大的身體,支離破碎,好像一個熟過了頭的西瓜,血濺了我半臉。
我轉身以自己最快的速度翻過去,七星龍泉奔着那個青色絲緞就削了過去,可沒想到,那“青色絲緞”比看上去要堅韌多了,這一下竟然沒削破!
不光沒削破,那個絲緞還跟活了一樣,直接把七星龍泉卷住,力道又快又狠,幾乎把七星龍泉直接卷走!
我大吃一驚,玄武局就能養出來這種怪物——要是真龍穴裡的,是不是更……
可腦子也隻是這麼一轉,根本來不及細想,我立刻引了行氣上誅邪手,太歲牙在右臂上起了作用,反手把七星龍泉抓緊,青色絲緞跟七星龍泉膠着住,那柔婉的聲音像是十分滿意:“郎君沒變。”
下一秒,她那絕美的面容繞過來,我猝不及防就跟那雙美麗的眼睛對視上了。
好美。
身體像是失去了控制,不想動,隻想就這麼沉溺進去。
“你來……”
那聲音在耳邊輕吟:“松開手——你看看,手裡是什麼?”
我手裡?
眼角餘光穿過了越來越濃重的桃色霧氣,竟然看到,我手裡攥着的并不是七星龍泉,而是一截子臂膀。
我耳朵嗡的一下,那隻手很熟悉,手腕上,挂着一個銀絲镯子,是我上次去西川套圈套來的。
是很便宜的那種手工銀,戴久了就發黑,可啞巴蘭還是特别喜歡,戴上新鮮了半天,說謝謝哥,我勤擦着點就行。
暖,軟,潮潤。
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恐懼,我是什麼時候,把啞巴蘭給……
在那種激烈的刺激下,我渾身都涼了,手一顫就要松開,可就在要松手的最後一瞬間,一個東西忽然撲了過來,對着我大叫,像是在阻止我。
這個龐然大物,是剛才被打壞了的“胭脂原料”?
詐屍了。
還要咬人?
我左手對着那東西一劈,就起了殺心。
但是——腦子忽然就有了一絲極其不易察覺的違和感。
我總覺得,哪裡不對。
就在這一猶豫裡,又一個行屍對着我撲了過來,這個行屍很纖細,纖細的甚至像是個女的。
他也在大叫,不過,聲音撕扯的像是音頻亂碼,我隻覺得刺耳。
“快點!”那個柔和的聲音催道:“不打死它們,它們就要咬你……”
是啊,我是該丢下那截臂膀,劈開面前的行屍,可那一絲違和感讓人如芒在背,總是不舒服。
我得想起來,到底是哪裡不對。
“嗷嗷嗷!”
那個行屍喊的更厲害了,上來就要咬我,沒法考慮了,非劈開它不可!
可就在左手引氣削過去的一瞬,我腦子裡斷了的線,忽然就續上了。
我知道哪裡不對了。
行屍,是不會嗷嗷叫的。
這個想法像是一陣北風,倏然就把腦子裡的桃色迷霧全部吹散,就在纖細的行屍要護住怪叫的行屍的時候,我手在最後一刻改了方向。
“啪”的一聲巨響,一股子木屑的味道炸開,木頭渣滓濺了我一臉。
果然,我面前不是什麼行屍——是金毛和啞巴蘭!
那一下,幾乎是齊着金毛的頭頂削過去的,半指頭長的犼毛齊刷刷落在了地上,裡面還摻着半尺長的青絲。
金毛看我明白過來,高興的就在原地兜了個圈子,啞巴蘭也喘了口氣,一屁股坐在了地上:“哥,你,你丢了魂了?”
啞巴蘭的四肢,都是完整的。
卧槽,我一下就反應過來,重新看向了右手,一顆心才重新落下,跟從噩夢裡醒過來一樣——我右手裡也不是什麼啞巴蘭的斷臂,就是險些被我松開的七星龍泉!
面前的青蛉,那個絕美的面容,不由就是一個難以置信。
這個被魅惑的感覺,跟大山魅極其相似,卻有所不同——大山魅是要你迷戀上她,失去反抗能力,可青蛉不一樣,她能把你看到她想讓你看到的幻象,通過幻象,把變成一個傀儡,讓你做任何她讓你做的事情。
比大山魅,還難對付!
蓮子在一旁拍手笑了起來:“郎君,早跟你說了——青蛉姐姐很厲害的,你瞧見了不曾?有青蛉姐姐的眼睛在,多厲害的客,也逃不出去!”
青蛉掃了蓮子一眼,蓮子這才意識到自己可能不該多話,吐了吐舌頭,但她似乎并不明白,為什麼不能多話。
不愧是能把熊皮人給纏住的本事。我說熊皮人怎麼這麼簡單就被抓了,肯定也是中了這種幻象。
剛才,差一點就把金毛和啞巴蘭給……
景朝國君那個死王八蛋,他的債,憑什麼全算我頭上?
既然給你背債——那我身上那些疑似跟他有關的東西,就當他給我的補償了。
那道子金氣猛然逼上了眼睛,眼前瞬間跟起了霧氣的擋風玻璃被雨刷擦幹淨一樣,與此同時,那股子劇痛讓身體猛然翻起,我一下就清醒了過來。
那個痛,幾乎要把眼睛削薄了一層一樣!
而對上了我的眼睛,青蛉的眼神,猛然一空——像是想起來了什麼事情。
而抓住了這個機會,“嗤”的一聲,那些青色的絲緞,全部撕裂,金光猛然穿透,七星龍泉的鋒芒對着她就削了下來。
青蛉大吃一驚,身體以人類達不到的柔軟程度翻轉,羅裙下一個巨大的長尾乍現,奔着我就橫掃了過來。
我擡起腳,一步踩在了長尾上,她更是不可思議,擡起手,數不清的絲緞不知道從哪裡延展出來,對着我就卷——破風聲刮的臉生疼。
可因為那金色的氣——我比她快。
在被青色絲緞包住的前一秒,七星龍泉金光炸起,絲緞全部撕裂,鋒芒就落在了她美麗脖頸錢一寸。
她的眼神凝住了。
可那種金氣給身體帶來的劇痛,從額角延伸到了全身,幾乎承載不住,我聽到自己的聲音,開始氣喘籲籲:“我們的人呢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