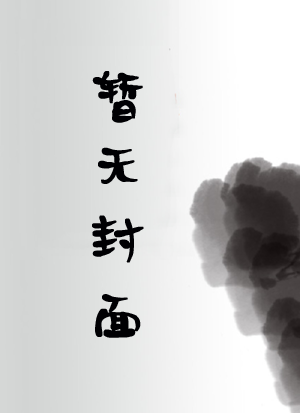程星河一愣,立馬抓住了對講機:“你他娘放的什麼歪嘴屁?什麼叫走不了了?一會兒等着讓海浪給卷沙子底下去?”
“不是我說的。”蛤蟆鏡的聲音顯然也有些發抖:“是二妹娃說的——她說,船怕是有點問題。”
剛才還好好的,能有什麼問題?
程星河皺起了眉頭,看向了二妹娃,又看向了我:“不會是——二妹娃不想走,故意找個借口吧?為了自己的男人,拉咱們一個船陪葬,可不怎麼厚道。”
趙老教授也知道了來龍去脈,歎了口氣:“這姑娘也是情深義重,小孩子嘛,心智不成熟——順軒。”
他一個小元寶手的徒弟立刻過來了。
“叫咱們船上的船工上他們那邊看看去。”
被稱為順軒的小元寶手立刻下船艙找人,上了小白腿上。
現在已經三點五十了,再回不去,怕真就有點危險——畢竟水文先生的預測我們都看見了,一秒都不帶差的。
程星河擺着手指頭算了半天時間,算的跟醬豆腐一樣,我讓他沒事看看幼兒園教材。
他正要還嘴,對講機就響了起來:“老師,咱們船工也說,确實是出問題了,這船走不了了。”
蛤蟆鏡一下就急了,他有錢是有錢,這個船也不是一般的船,誰也不可能就這麼扔海上。
說着就看向了二妹娃,顯然疑心這船出問題,是二妹娃動了手腳。
不過二妹娃面無表情,一聲不言語,似乎這地方的一切,都跟她無關,她隻看着那片埋了麻愣鞋的海。
我回到了小白腿上,就勸他,命比财産重要,搭趙老教授的灰船回去算了。
有錢人都惜命,蛤蟆鏡沒辦法,隻好答應了下來,一幫人挪到了灰船上,啞巴蘭還挺慶幸:“幸虧咱們這還有一個備用的船,不然就真交代在這裡了。”
唯獨白九藤表情還是不好看。
安頓好了,灰船上頓時就擁擠了不少,船工去開船,可半天也沒動靜。
程星河一個勁兒看表:“不是,他到底磨蹭什麼呢?”
不長時間,那個叫順軒的上來了,臉色已經白了:“老師——咱們的船,也壞了!”
趙老教授一愣:“你說什麼?”
那個順軒看向了被我們強拉過來的二妹娃,臉色頓時漲的通紅:“你!是不是你?弄的你們小白腿走不了,還把我們的船也弄壞了——你想死自己下海,别連累我們!”
二妹娃冷冷的看了順軒一眼,忽然一轉身,就要從灰船的船舷上跳下去。
我一把抓住了她,程星河也是:“姑奶奶,什麼時候了,你還有心情以死明志?”
趙老教授也被驚住了,張口就想勸二妹娃,可這一瞬,趙老教授自己的臉色也難看了起來,一隻手,死死抓住了自己那條被六指抓住的腿,豆大的汗珠順着額頭就往下滾。
白藿香看出來了,立刻給趙老教授紮針。
可白九藤在一邊事不關己的說道:“這是鎖魂印,治不好的,别白費勁兒了。”
那個叫順軒的徒弟立馬問道:“這什麼意思?”
“意思就是,抓他的,遲早要把他給拉下去呗。”白九藤盯着這兩艘船,眯起眼睛:“不好,不好,很不好。”
我立馬看向了順軒:“你先說說,船是怎麼個壞法?”
順軒反應過來:“兩個原因都差不多——說是啟動不了,像是發動機被什麼給纏住了。”
纏住了。
我把避水珠含在了嘴裡就下去了。
不長時間。程星河也跟下來了。
我們一到了船底,頓時都皺起了眉頭,互相看了一眼。
人臉藤。
兩艘船底下,竟然是密密麻麻的人臉藤!
果然,世上就一種東西,能短時間之内長這麼大,足夠把巨大的船給困住。
而那些人臉藤,面色紅潤,眼睛微微睜開,顯然是剛喝飽了養料。
這可不是二妹娃能做到的,是底下的東西,舍不得讓我們走。
我甩開了斬須刀,對着那些人臉藤削過去,哪怕人臉藤堅韌,可在真龍氣之下,啪的一聲,炸的到處都是。
程星河很高興,給我比了個大拇指,可我看出來,沒這麼簡單——船底下的木闆裡,還有人臉藤的根須。
這玩意兒一絲根須就能活,不搞幹淨了,半路遇上什麼海裡的靈物吃飽了血,還是會抛錨。
我沒法子,隻好剔除了起來。
兩個大船,工作量不小,把啞巴蘭他們也喊下來幫忙,這才弄幹淨了。
再一上去,心裡已經有了不祥的預感。果然,白九藤已經盯着自己的表說道:“快五點了!”
離着風暴起,就還剩下一個多小時了,而我們得花三個小時返航。
還能怎麼辦,趕緊呗!
上了甲闆,船工開船,二妹娃一開始有些不情不願,她一雙眼睛光看着我,顯然還想管我要避水珠好下去救人,不過她也知道,一船人的命在她手裡,一言不發,就去開船了。
船以最快的速度往回趕,不過一返航,就看見一個很大的輪廓靠近了。
也是一艘船。
說起來,今天跟我們一起到了這種遠海的漁船幾乎沒有——都聽見了水文先生的話,生怕七點之前趕不回來。
對面那個船極大,顔色發烏。
他們要是這個時候,上水神島水域,也會倒黴。
都看見了,自然不能見死不救,我讓二妹娃嘗試跟他們取得聯系,可程星河一把抓住了我:“聯系個屁——你瞎啊,沒看到那個船上頭是什麼?”
這個時候,海面上已經升騰起了一層白霧,越過白霧,我看到了那個船的桅杆。
帆船?但是再仔細一看,我也皺起了眉頭。
那個船有尋龍角,鳳凰頭——絕對,不是這個年代的船。
像是,古裝劇裡穿越出來的!
二妹娃轉過臉,看清楚了霧霭重重裡的船,吸了口涼氣。
她處變不驚,隻露出過兩次失态,第一次,是看見了麻愣的鞋,第二次,就是現在。
“走不脫了。”她喃喃的說道:“這是——水鬼船。”